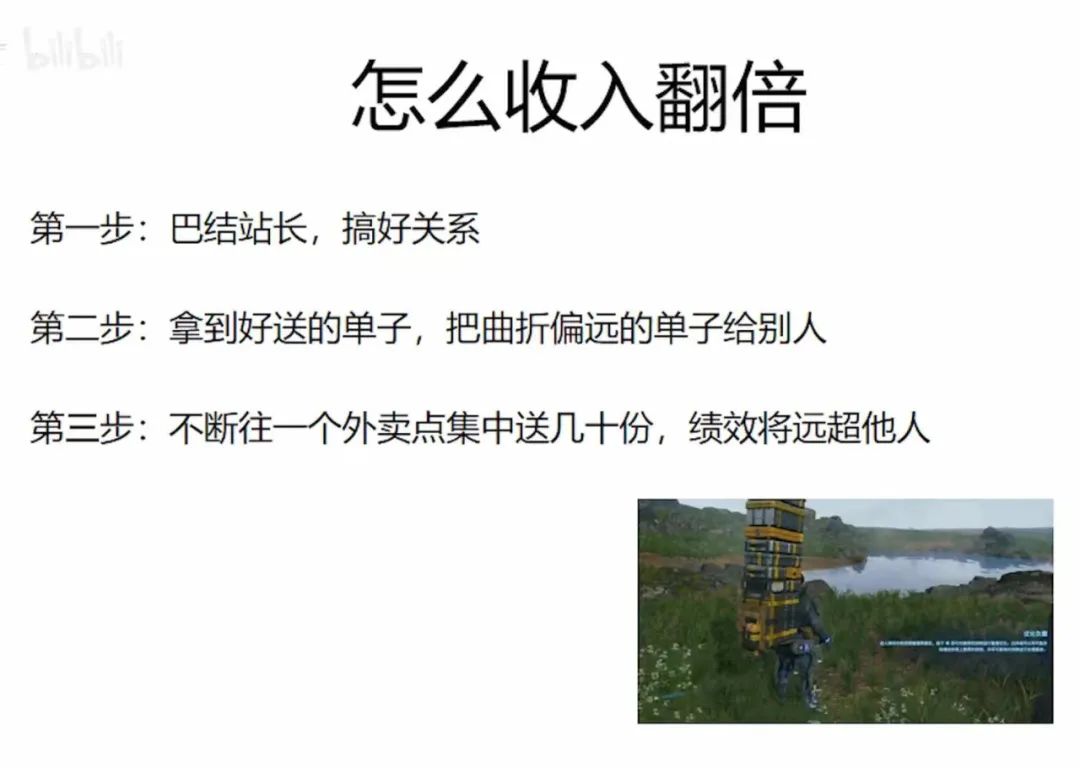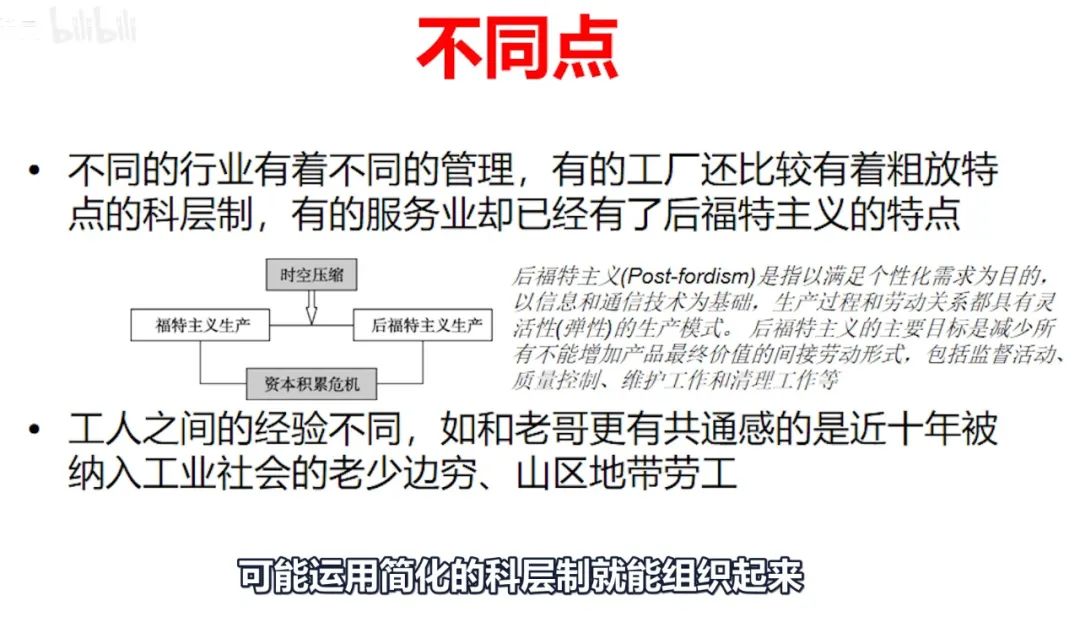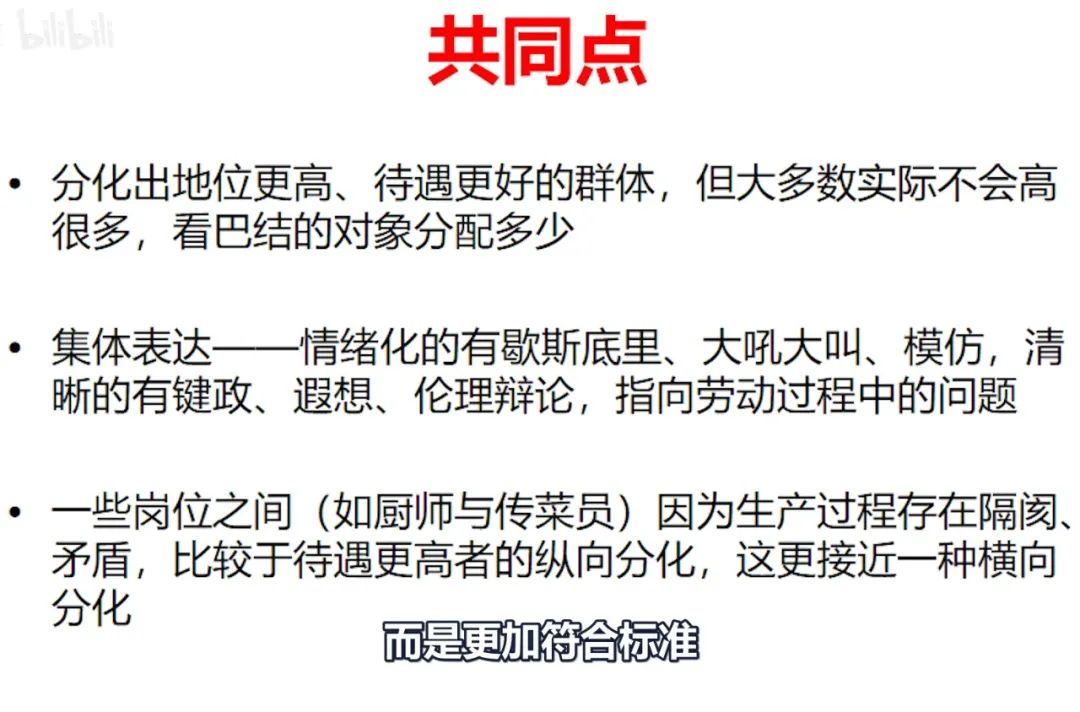采访西北工人——走出大山以后,他们过得怎么样了?
来源网站:mp.weixin.qq.com
作者:多思悌劳动观察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打工人, 流水线上, 老哥, 骑手, 工资, 老板, 站点
涉及行业:制造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河南省
相关议题:工人运动/行动
- 西海固地区的打工人通过易地搬迁和务工经历了从自然的绝对贫困到资本主义相对贫困的转变,体验了从感性到理性的打工过程变化。
- 打工人在大城市的工作经历中,面临着机械性重复的劳动和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束缚,但仍努力寻找个人主动性。
- 在工作场所,工人之间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情感交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集体性和团结意识,尽管面临流动性强和集体条件缺失的挑战。
- 打工人在外卖行业的工作中遭遇体罚和管理上的不公,但通过个人和小团体的努力争取到了一定的改善。
- 老哥作为一名打工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对同伴的帮助行为,展现了打工人群体中的互助和善意,即便面临收入微薄的现实。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Dooste Labor Review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B站视频《》的文字稿。视频的内容是up主“挖枯乐园”在采访了一位西海固地区出身的打工人后对访谈内容的整理和评价,在征得同意后将文字稿发表在这里。
▼点击下方图片可直接观看视频▼
B站关注UP主挖枯乐园谢谢喵
1.
2021年,一部讲述西海固的人民从贫瘠的土地完成易地搬迁的电视剧《山海情》上映。剧中对贫穷的描写让人们深入了解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家徒四壁。随着经济的扩张、政策的推行,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开始进入了工厂和城市务工。所以在河南的走访之后我非常好奇对于西部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于是我采访了一位来自西海固的打工人,想向他请教一下近年的打工经历,了解一下这些年的基层生态。
提起西海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穷,它在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一位西海固诗人这样写道“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
20年,有“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不过对于进城的务工者来说是新故事的开始,我的关注点在于,一种基于自然的绝对贫困,被资本主义转化为一种相对贫困所发生的变化。在时代变化之中,工人又是如何反应的。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会以老哥代称这位工友,并且隐去部分信息。整体的内容我认为主要可以说是游侠式的冒险,里面还有几次斗争,是许多人平时遇不到的。
我和他是在大城市里认识的,他有着一手熟练的电焊技能,会驾驶叉车,属于面板很立体的打工人,当时他还在四处游历,打完工后旅游徒步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相识后没有时间系统地梳理他的经历。他以前开了几年叉车,当了几年焊工,后来都因为工资谈不拢离职了。老哥是西海固人,他从小会跟着母亲去城里。母亲是建筑工人,副业从事家政服务的清洁工工作,会去办公楼等地做清洁。
在几件事上可以了解到什么叫物权概念的模糊,因为贫穷存在偷井盖以及小偷小摸的习惯,母亲对此并不觉得是偷,反而觉得是会过日子的体现。有一次,老哥带着几个儿时伙伴翘了个井盖,因为太重了小孩搬不动,几个人就滚着井盖把这个铁坨坨滚回家了,母亲当即表示赞赏,太懂事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由于以前一些地方根本没有见过公路,只有一些土路,所以进城看到井盖可能并不会觉得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反而会认为这是没人要的铁坨坨,可以顺回家补贴一下生活。平时会像一般家长那样教育孩子不要偷窃,但把这个模糊地带的铁坨坨带回家是“生活”,这是当时城乡差距的一个体现。
与此同时,一种人压迫人的视角从小就被植入了,因为当年的许多穷人会去摆摊,城管队伍往往成分比较混杂。经常会出现城管打人的事情,于是老哥从小就耳濡目染,哪个同学家长被城管打了,就在某条熟悉的街道隔壁又有城管打人了等等。另外,过去的当地学校有一些富二代,家长可能是当地豪强,富二代就喜欢欺负同学,会出现踢球的时候把人弄倒,然后压在地下踢的霸凌。因为富一代在当地比较有权势,被踢的同学家长还要去向这个土皇帝道歉。
陕甘宁地带的务工人员同样会进入一些省内中心城市务工,支撑起当地的工商业。现在老哥在一处县城的餐馆工作,而在当地有着许多因土地流转失地的农民。当地有着几处试验田,一旦有收割机开动,就会有农民等收割机开完了,过去捡掉落的农作物。因为捡的人有一定规模,所以试验院校与农民之间有互相的默许,你的收完了我再去捡。老哥表示,这样的分化在学生里也能看到,在类似他所工作的餐馆里,往往有许多职校生在那里兼职,而大学生确是各种餐馆的消费主力,他们的收入直接来自较富裕的家庭而非当地工资,以至于消费水平往往比居民要高许多。
老哥的观察十分准确,我很好奇他的探索欲与其他人的不同,别人可能并不是想继续寻根问底。他说自身在出了学校后,进入社会工作,身份转变给自己带来了积极变化。因为在学校比较压抑,成为工人以后感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有了更多安全感。以前自己未必能想那么多,他说经历了从感性的打工到理性的打工的变化,他可以清晰认识到一些自我身份和社会结构的问题。作为从小放羊的人,他感觉到工作有种像羊一样被赶来赶去的被动感,这样的山区经验也让他与广西、云贵川地带的工人有倍感亲切的联系,很快就能混的很好。他也厌恶机械性重复的工作,他这样和我说“留在一个地方打工,恰恰是更被动的,身体被绑在工作岗位上,心却被流放在了麻木的荒原”,“但是我恰恰又是在有意识的从一种被动的生活状态中,寻找并夺回自己的主动性。”
令人惊讶的是,他虽然认为生活属于自己,可自身的生活其实是较少的,不怎么爱好娱乐,也没有烟酒的习惯。与许多工友一样他的收入比较微薄,不过令我非常震惊的是,他非常喜欢为别人花钱。他经常庇护一些年纪小的工友,以及资助一些生活有困难的人,他自嘲为大撒币。有的人会感谢他,也有的就不会记着撒币的恩惠,个别还会找他爆更多金币。老哥和我说,累计下来他可能已经撒出去了三万块,这对于从事体力工作的工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此行为,老哥的对象表示强烈谴责,钱花出去人家还不记着你,还觉得你好要钱,以后不许再撒了。
2.
和许多流动性很强的工人一样,老哥的工作很少超过几个月的,但他积累了各式各样的技能,他也有时间去践行自己的爱好。从去年开始,他就开始了徒步,计划从湖南一直走到深圳。很多有名的骑行博主可以带货赚米,他徒步到深圳以后就去进厂打工了,开启了这几个月的冒险。在深圳,他进入了某知名的电子厂打螺丝。厂内生产cpu处理器,主要在流水线上进行装配、包装等工作,一工作动辄十小时以上。如此的工作带来的麻木是表面的,积累的情绪总是会在一些时刻流露。老哥说有次他们那个组内互相之间开玩笑,大家原先边干边互相逗对方,逗着逗着有人开始说我们是牛马,大家哈哈一乐随后学起了动物叫。我是牛,他是羊诸如此类,最后有人学起了狗叫。叫了一段时间后气氛从欢乐转变为了悲苦,越来越多的情绪进入叫声中,有人为此流泪,毕竟真的是牛马。
除此之外,有时大家在流水线上还会畅想魔幻的未来,比如厂里要是大家都停工了,你要不要去把什么设备给搞定了,要是起了冲突怎么办,你要不要去前面先顶着,大家还会辩论在法律风险下要不要把带头人供出去的伦理问题,有位女工友以前面对过一些类似的情况,表示不能把人说出去,听闻有人想交人会生起气来,怎么可以把人交出去呢。
大家其实在工作之余乐意进行一些精神交流。所以在流水线上,即便流动性很强,仍然存在着最低程度的集体性表达。依然有人会根据原来的经验、原则,表达出善意和团结。如果我们过度强调今天的工人流动性强,以及各自没有原先国企工人的集体条件,是否会模糊一些工人群体自身已有的认知呢,好像他们就没什么团结的可能了,团结起来也无法维持下去,以至于“原子化”的人无力做任何事。这点把工人阶级的潜能与现实遇到的障碍混同了起来,二者本就是对立的,否则好像眼前的障碍就是极限,好像能达到的极限必须在障碍之内,永远不能跨出现实的围栏一步。于是原子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我们不能拍脑门就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太远了,不看群众之中已经存在的最低认同,我认为这件事上值得深究,老哥后来的一些经历也有比较鲜活的表现。
3.
后来他的对象因为工作的变动去了东部沿海某城市,老哥就辞职一起去了。他在那里开始做骑手跑外卖,工作场景虽然换了不过工作感受变化不是很大。他们几个骑手有个宿舍,同样一辆车大家轮流开,你送累了回去躺着下一个人接着上,许多人工作时间和强度还是很高,个别身体好的能干到十二小时以上。虽然骑手中专送和众包有区别,但仍有许多人一手专送,另一手送众包,众包真的成为了一个副业收入,于是两手都抓的骑手不得不起早贪黑不知疲倦了。
骑手工作一般有那么一个站点,骑手早上在站点集合开会,此时站长给骑手打鸡血,另外也会对一些违规的骑手进行批评和惩罚。老哥所处的站点会进行体罚,不会直接殴打但涉及一定的服从性测试,站长会让骑手做俯卧撑。在俯卧撑期间不仅周围行人众多,而且站长会故意站在受罚者的头上方,仿佛骑手在受胯下之辱,具有一定的侮辱性。之后在老哥的个人交涉下,站长承诺不再进行体罚,写下承诺书,不过老哥后来的部分工作仍然存在体罚,经常会有做俯卧撑以及做仰卧起坐等现象。在某些工作里,体罚是普遍存在的。
当然在外卖站点中不止是个人的斗争,还有骑手自发的搞几个人的小团体和站点搞斗争。为什么骑手和站点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呢?首先在于站点的管理喜欢进行惩罚,来控制打压工人,如进行罚款或者之前所说的体罚。罚款也不是明着说,从工人的钱包里扣,而是隐性的计算,从工资里扣。一旦违规就会让名义收入减少,而且大多数人其实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扣钱。另一方面则是站点之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可以利用算法和权威谋得更高得社会地位。在骑手之中是存在月入过万的人的,但是这些人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勤劳。
而是一种被扶持的典型,如老哥所在的站点中存在着一个月入三万的骑手。他的收入是怎么被算那么高的呢?因为他搞好了和站长的关系,他就可以拿到集中送的几十个单子,这些一般都是放在柜子里的。也就是说集中拿单子,一次在一个外卖柜中全部送掉,送一次就是别人的几十倍。那些关系没搞好的骑手,则会拿到各种各样走歪路的单子,工作的十分折腾,分化就这么形成了,有人累死累活拿几千,个别能被扣到倒欠钱,而另一些人凭关系能拿几倍的工资。站长也向老哥“索过贿”,向他暗示要求送条烟或者请吃饭,其实就是常态性的给好处,把他当成大哥那样供着。当老哥拒绝后,站长表示“你不会来事”,就去提携别人了。最后老哥和许多“未被提携”的骑手就自然而然玩到一起去了,与站长和他的小弟们产生了矛盾。
“小团体”虽然和站点有冲突,但没有采取停工等手段,工人自身具备评估风险的考量,整体环境如此这不是几个人能改变的,最终依赖的是集体谈判。老哥对我表示,谈判也是自己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工资经常被拖欠不谈不行,部分工友不去要工资就忍着了,等到忍不下去才会交涉。斗争的结果呢?最终“小团体”成功被站点拉黑,把占一半人的骑手账号踢出站点群组,最后剩下的一半人看这个样子也一起走了,虽然大家离开了站点让站长的绩效吃了亏,至少是一次战术胜利,但生产场所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变化是发生在生产场所之外,最终也只是大家各自结工资,这也是大势的限制。
4.
经此一役,老哥准备一个人去自驾游,他刚拿到驾照,这也是他第二次出发长途旅行,我想也是毕竟那样的工作一定很消耗身心,只是我低估了他旅游的距离,他从广州出发一路开到广西的边境。在广西农村里他参加了当地的庙会,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吃席,后寄宿在当地人家里。给老哥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寄宿的人家很穷,屋里都不算有像样的摆设,他们是做村里墓碑的,平时还会被同村嫌弃晦气,征地后只拿了几百块。寄宿的人家给人留下了一定的贫穷形象,与经过的庞大化工厂相比,这个问题又好像显得十分渺小。
在经过海边的时候,老哥和当地人一起捡海边的生蚝,可以直接一口吃下去。如果想加工一下,可以拿喷火枪烤着吃。然后老哥又遇到了一批渔民,抱着出海看看的心情,他上了船和渔民们一起出海。渔民使用的装备十分简陋,用着这些装备他们就下水,插个管子就下去捕捞了,一抓就是三到四小时,当然他们会上来几次。他们管抓的统称为贝类,其实种类各式各样,主要是螺、贝还有螃蟹。出一次海他们能挣300—1000左右,看上去比较多但还有维护费燃油费的支出,一个月一般考虑天气可能出十几次。往往一船的都是同乡,没啥防护就下去了,这个工作其实是有风险的体力活,平均下来一个月可能赚个六千以上,这点绝对是应得的。大家对老哥也很热情,晚上吃的就是刚抓的,一顿可能一起吃掉了五六百块,绝对是一顿夸富宴。
这些旅行经历,也构成了老哥的思考,就是当地的百姓很热情,是一种群众之间跨地域的互相理解。但是老哥又经常了解到一些地域上的歧视,打工的时候互相之间也会传一些地域印象。老哥自己也可能遇到几个工友会欠钱不还,会半夜起来偷钱,确实容易形成一定的偏见。以上的例子造成歧视的原因还是十分经验性的,另一种就比较根深蒂固,完全是一种等级排次的鄙视链,如认定某地的人就是低人一等,形成不同人是有不同等级的观念,这样就比较难处理了。
玩好了要继续上班了。那么下一份工作是什么,我完全没猜到,老哥去矿上上班了。矿工是比以上我们提到的工作要累得多的,一般矿上月休五天,但是大部分工人其实上不满规定的班次。因为工作内容是比较累的,干一天以后就躺一天,如此循环也就一个月十五个班次。上不满指定班次就要扣五百,大多数师傅也就扣了,最终一个月能拿五六千。老哥进的是掘进队,这也是大部分新进矿的人从事的岗位,有时也会有较为年轻的工友进入。掘进队就是负责打通通道,有人用风钻钻岩壁,有人固定岩壁建巷道,老哥是负责把掉落的石头铲进矿车,然后运出去。这是比较辛苦的,而且矿井里和地面上的粉尘如果吸入过多都很容易得病。
矿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分化,有一批人就是监工,也就是俗称坐办公室的,他们负责监控进度和管理工作,他们多数是本地人,他们一半的领导是半文盲状态,有几次签字的时候要工人代签。所以只能说,他们能在这个岗位一定是具备一些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条件,过于优秀了。与之相对的是,矿工们经常性在休息场合一起围着坐,聊历史评人物,几个老师傅会在某些经典议题上做出评价,其内容可以说就是在鉴证。在这个矿上,工人的知识水平与监管者颠倒了过来,一方可以千秋功罪我们评说,另一方连笔都不会握了。这个对比下,不如干脆让老师傅去管算了,有的活看上去是人都能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非常遗憾的是,这么有趣的地方老哥没干多久已经要跑路了。他在矿上还没干到老师傅一个月的班次就跑了,虽然矿上很累,但更加让人吃不消的是拖工资,所以老哥果断提桶跑路。与外面的小黑厂相比,矿上至少明着说我们这个月发不出。
在老哥的再三要求下,矿上在他离职后结算了工资。这也是他的底线,一定要把工资拿到手,有时他还会帮助工友一起要,但一般只会发他一个人,对其他工友也是拖欠时间较长的。
5.
在离开矿后,老哥来到了西北某县城,他找到了一家烧烤店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店算是比以上工作要离谱多的,可以说是踩到地雷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老哥发现这个老板他也欠薪,并且有着地头蛇一般的做派,员工中传言有人问他要工资,被他拉到监控盲区叫人围殴,可见这个老板是什么形象。然后由于老哥也被拖欠,他选择在店铺里与这个老板谈判,希望离开前结清工资。不过这个老板听到要求以后表示“我不会发你一分钱工资,我xxx但凡发你一分钱工资以后跟你姓”,随后马上开始威胁老哥,并且做出要打人的态势,可见他已经轻车熟路了。老哥就赶紧表明我已经在录视频了,并且高声喊话让周围人都能听见,如你怎么要打人此类。最后老板看周围人比较多不好下手,只好口头威胁你赶快把视频删了。最终老哥出于考量选择报警,在警察来之后老板其实并没有消停一刻,仍然非常狂妄。在派出所里当着警察的面说什么“我砸钱也陪你玩”“你以为我这么多年在这咋混的”,又对着助理说大不了我直接花钱把他砸进去。他在派出所大厅里说这些话,老哥肯定表示视频我不会删,如果你威胁到我,那就会有人发出去。
在一系列纠缠之后,老哥离开了那家烧烤店,结果是老板把工资发了。这个结果让店里员工非常开心,因为老板拖他们工资,这次却有人能把工资要到手,老哥还会和员工互相调侃,他发我工资了那他现在该跟我姓了,员工则会回道:你等着马上他就砸钱把你弄进去。最后其实只有老哥一人拿到了工资,其他员工还处在被拖欠的状态。目前老哥换了一家餐馆,由于那家餐馆使用了原先某大品牌的管理模式,所以老哥始终不能适应那里高度服从化的工作。他总是抱怨店里逼着人要微笑,要露出几颗牙齿,指标没做到还要在群组里发红包,大家戏称为付费上班。看来这家可能也待不久,我问老哥以后要去哪,他说钱攒够了想继续旅游,上一次钱不够了,现在准备继续下去,去云贵看看,去东南亚看看,等回来以后可能去利用汽修的经验去汽配厂。所以这就是老哥不到一年的集邮式打工生活。
6.
在许多工人那里都存在着相当丰富的经历,那么在老哥的这些经历之中,有哪些异同点。不同点在于,不同的工作有着各自的生产管理方式。比如工厂之中,可能运用简化的科层制就能组织起来。但是在餐馆就会更加复杂,尤其是引用了所谓先进经验的餐馆,他们会出于分工有各自的组长,有经理划分管辖范围。还有就是工人之间的地域、年龄、性别、经验等因素形成的差异,导致各个地点的工人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最大公约数,有着各个鲜明的特点。比如厂里的工人会有着不能出卖人的伦理标准,但部分餐馆中存在着顺从巴结经理群体的“趋炎附势者”,他们不会认为自身和周围人是一样的,会更加谄媚地顺从上级,会把脏活累活交给下级,使自己能够有较高的待遇。
在认知上,县城的环卫老工人能够以清晰的线性脉络,从六十年代开始理清自己的经历,而工作时长很高的物流普工会每天工作得晕头转向,很难以清晰的脉络整理记忆。煤矿里的老师傅可以谈论天下大事,但换做职校生兼职的服务员则会认为于己无关。其中的差异不能过于的生活经验化,否则好像全世界就是只有周围几公里或周围十几个人那样,好像工人阶级的形象就是某个固定的形态。所以我们无法用过度共情、过于经验的方法从一些个体身上发掘出什么,社会的真相并不在那里,关键在于那些个体们在一整个政治经济网络中汇集成了什么。在此之后,我们再看该从什么角度把握这些丰富的经历,去认同去团结形形色色的工友。
老哥的这几份工作中有着鲜明的共同点,最首先是这些工作都明确分化出一批待遇更好地位更高的工人,这些人的统一特点并不是更加勤劳,而是更加符合标准,他们更加依附于如经理、领导的权力,所以是他们的小弟是自己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特别待遇。他们不会将自己当成是什么打工的,或者所谓干活的等等,自己并不与他们平等,而是习惯于攀龙附凤,去指手画脚去命令人。煤矿里会有关系户能把舍友挤出去霸占宿舍,餐馆里会有人朝来视察的领导挤眉弄眼,其中唯一靠这点更加巩固经济收益的群体只有站长和样板骑手。他们认同上位者高过认同工人的身份,自认为“会来事”就能谋取利益最大化,实际是对上位者有不现实的幻想。
另一点是,在这些地方都有非常鲜明的集体表达。在流水线上大家会学动物叫,矿上老师傅带大家鉴证,还有我没有细说的一件事是一个餐馆到晚上大家会敲锅呐喊来发泄,边敲锅边骂老板,如老板就是个xx,我天天这样工作如何,他会干么?所以许多工友经常写非常简单的生活感悟,这其实是已经开始的语言化。劳动过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无法以明确的符号表达出来,好像这只是干活必然有的挫折感,好像天然的得认命,那压抑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类似集体歇斯底里的情况。然后语言化程度比较高的就会变成正式的议事讨论和分享,如矿工鉴证那样。如果没有集体表达的渠道,那些个别的情绪就会容易变成暴躁的互相攻击,有的厨师和传菜员就会互相骂,直到差点打起来。
另外拖欠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老哥虽然经常只有自己一个人要到钱,但是可以说是非常有经验了。他说自己非常有底气能拿到钱,可以说有百分百的把握,但其余工友经常要不到。老板发现有底气、淡定的人,会觉得遇到有经验的就给了,做不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要到。老哥有次自己要到后就被老板造谣,说什么他已经被抓了,你们别要工资了来吓唬其余人。所以比较成功的手段,基本依靠的是谈判,以及对工友的团结,比较团结的就能做集体的谈判。令我比较吃惊的是,老哥几乎没有做过劳动仲裁,主要是因为劳动仲裁的时间,他给我举了个生动例子,劳动仲裁就像是一张牌,工人能打老板也能打,有的老板也会说去仲裁,但不了解的工友可能就被唬住了。我们打出这张牌是为了让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天平多向工人这边倾斜一下。换言之如果效果不好,就不出这张牌,所以老哥对仲裁是一种了解不亏,未必使用的态度。我认为将仲裁等手段当作是工具性的,而非完全规范性的,这样的态度更加实用也让更多人人容易接受,天平朝向哪里关键还是自身能不能团结,懂不懂抱团,个人心里有没有底,有没有争取自身权益的勇气。否则人家用点自己不懂的手段,让人拿不到钱生活难以维系,可能就不攻自破了。
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对老哥一年不到的游侠生活进行的总结。我无法清楚明白地说清楚其中的经验和事件是否普遍,因为其他地方我不好评价是否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毕竟我也没去过。无论是收入不高,缺乏工作场合中的尊严,激发出某种压抑后的表达等等,让人只能想到两个词,一个是“代价”,另一个是“边缘”。越来越庞大的商品堆叠下代价最沉重的人,也是形形色色话语夹缝中的人,唯独还不是顶天立地的人。
最后我想以老哥的一段话结尾,这也是他四处集邮打工的本心,我认为相当深刻因为他没有将四处集邮当作闲暇时期的玩乐,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事业:“如果不打破舒适圈,去了解更多的千千万万的打工人,那么就很容易什么都不知道,圈地自萌。一个真正的冒险家,永远只是为了获取征途中的宝藏,而委身于冒险,而不是像挥舞着木剑,却从来没有架船出过海域的小孩那样,憧憬于冒险的奇幻,却将冒险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
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
同时也欢迎投稿
多思悌劳动观察
"你将看见,他们也将看见"
欢迎投稿至邮箱